案例评析人:王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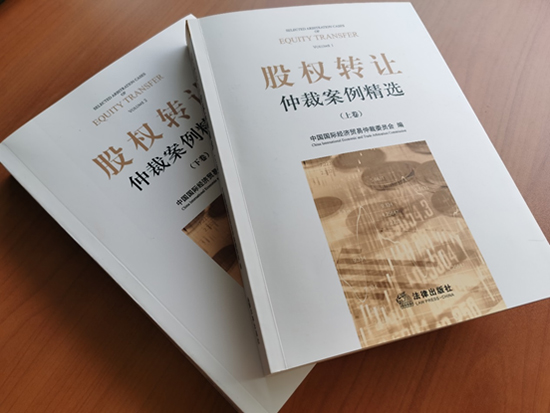
【关键词】优先购买权 股权转让 合同无效
【焦点问题】侵犯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是否导致股权转让合同无效。
【焦点评析】本案的基本案情:被申请人为聘请申请人在标的公司任职,与申请人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转让标的公司5%的股权。与此同时,本案合同约定若申请人在聘用后的5年内离职,被申请人按照申请人支付对价的10倍回购股权。被申请人与申请人签订这一股权转让合同并未经过标的公司另一股东的同意,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被申请人亦没有为申请人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申请人在标的公司工作不足6个月后离职,后要求被申请人按照合同约定回购股权。双方未能达成一致,申请人提起仲裁。仲裁过程中,被申请人主张由于股权转让未经过另一股东同意,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围绕此项抗辩主张,双方在庭审中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
现结合本案案情,围绕法律适用的焦点问题,评述如下:
一、被申请人的主张——侵犯股东优先购买权合同无效说
为了保护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公司法》第71条为不同意对外转让股权的股东赋予了优先购买权。对于侵犯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之效力,学界和司法实务中有无效说、附法定生效条件说、效力待定说、可撤销说、有效说等多种观点。被申请人在本案中的主张属于无效说,即认为《公司法》第71条的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转让股权的股东违反此条的规定与第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无效的合同自成立起即无效,不按照双方约定的内容发生拘束力。如果仲裁庭采信“无效说”,被申请人将自动从股权转让合同中解脱出来,无需再履行转移股权、回购义务。
二、“无效说”之缺陷
仲裁庭经权衡本案证据及实际履行情况,认为法律适用方面采用无效说有一定欠缺。具体而言:
1.将《公司法》第71条视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依据不充分,“无效说”不具备无效之法律基础。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因当事人的约定而排除适用才称之为“强制性”规定。仲裁庭注意到,《公司法》第71条第四款允许公司章程就股东对外转让股权之规则另行规定。据此,《公司法》第71条系属于公司章程未有相反规定时而推定适用的规定,显然不属于强制性规定。
2.仅完成股权转让合同签订,未办理相关转让手续,侵害结果尚未发生,不构成无效所涉“恶意侵害”。股东与第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仅为该股东赋予转让股权之义务。公司股东名册、工商登记尚未变更,第三人还未实际取得股权。此时其他股东依然可以向转让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且该股东可以实际履行。因此转让股东与第三人仅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尚未对其他股东构成任何实际侵害,故也不属于双方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
3.若认定合同无效将导致交易效率低下。
“无效说”的实质是禁止转让股东与第三方先行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这意味着,即使转让股东可以预知其他股东不会行使或没有能力行使优先购买权,为了尽快达成交易,先行与第三方签订的转让合同也会被认定无效。只要转让股东没有在签订合同前收到其他股东明确的行权表示,转让股东就不得与第三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显然,这种观点将给高效的商事活动造成没有意义的障碍。同时,若不允许转让股东提前与第三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将导致优先购买权中的“同等条件”始终处于没有约束力状态,也不利于各方之间高效的推进交易。
基于上述各原因,仲裁庭没有采纳被申请人“无效说”之主张。
三、仲裁庭意见——“有效说”
本案中,仲裁庭最终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采纳了“有效说”的观点。《公司法》第71条之规定,旨在保护股东为了维护公司人合性而取得股权的优先性。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与股权转移具有分离性。股权转让合同,自双方通过签字或盖章等达成意识表示一致即开始生效,生效后转让人负有交付股权的义务,受让人负有支付价款的义务,受让人尚未成为股权所有人。股权转移,一般以公司股东名册变更为对内生效节点,以工商变更登记为对外对抗生效节点。由于两者的分离性,为了实现该条款的目的,法律可以在股权转移程序中介入以保护股东优先购买权,没有必要过早介入去否决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具体而言,公司股东名册变更、工商登记变更等程序,需要公司内部经过表决程序才可完成,股东不同意对外进行股权转让的,可以在此时提出异议。若公司表决程序未通知该股东或未尊重该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则股东可以主张公司表决程序的效力瑕疵。如果第三人因其他股东行使权利而无法取得股权,则转让股东因不能实际履行股权转让合同构成违约,第三人可以依照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向其主张赔偿损失,包括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如果股权转让合同直接被认定无效,则第三人只能向转让股东主张过失缔约责任,所能得到的赔偿仅限于直接的实际损失。
【结语】合同无效是合同不生效力的形式中最高级的形式,是法律对当事人意思自治较为深度的介入,因此合同无效仅限于《合同法》五十二条规定的五种情形。其中大部分情形属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对他人的个体利益侵害导致合同无效的,只有恶意串通这一情形。为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保持司法审判权的谦抑性,在面对合同无效的主张时,仲裁庭应当审慎的作出判断,尽可能考虑在合同无效这一选项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救济措施等。无十分之必要,不宜贸然地宣告当事人达成的合同无效,以此充分发挥当事人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