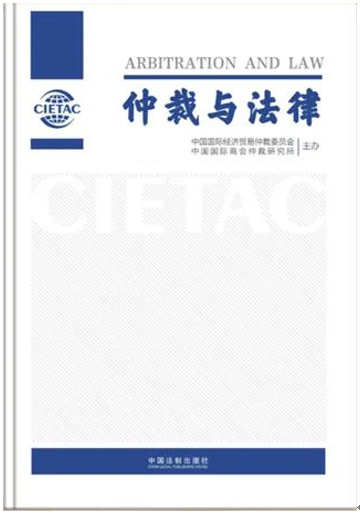
金挺峰*
摘要:网络入侵的层出不穷使得机密文件信息的获取成为可能,对于是否采纳此类通过非法方式获取的证据,国际商事仲裁尚未形成明确的判断标准。在现有商事仲裁规则与实践无法提供足够指导的前提下,审视与梳理投资仲裁庭的相关实践对于解决该问题或能提供诸多有益借鉴。总体而言,在自由裁量的基础之上,通过综合考虑证据的相关性与重要性、证据的真实性、提交证据一方是否亲自参与非法取证以及证据是否涉及特权制度这四个要素,商事仲裁庭能相对全面地对该问题作出判断。
关键词:国际商事仲裁 非法取证 可采性 自由裁量
一、引言
所谓地证据“可采性”(admissibility),原本源于英美法系的证据立法,是英美法下的特有概念, 1 大致相当于大陆法中的“证据能力”。证据的可采性是指其作为法律上的诉讼证据的资格问题,例如许多国家会在其国内刑法中规定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不具有可采性。不同于国内诉讼,国际仲裁并没有明确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之当事人可能具有不同法律文化背景,仲裁庭倾向于将重点放在决定争议所需要的事实认定上,而不愿先验地受到证据可采性规则的约束,阻碍其可能借以获取纠纷解决结果的任何途径。 2
然而另一方面,随着尖端科学技术的进步,网络入侵和黑客攻击变得愈加频繁,这一客观现状对非法取得证据之可采性提出了新的问题。以著名的维基解密网站为例,成立于2006年12月的维基解密是一个大型文档泄露及分析网站,各国的黑客均可将自己盗取的机密文件上传在该网站上,以揭露政府及企业的腐败或犯罪行为。自创立以来,无论在商事仲裁还是投资仲裁中,争端当事方多次提交维基解密公布的相关机密文件作为证据。多国政府对维基解密网站发出警告,美国认定维基解密泄露文件违反美国国内法, 3 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曾声明组建维基解密基金会和从外国窃取美国政府的保密文件是非法行为, 4 其创始人阿桑奇也被英国警方正式逮捕。如果黑客行为或者以维基解密为代表的泄密行为违反有关法律,那么通过这些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在国际商事仲裁中能被采纳吗?目前尚无统一答案。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以维基解密文件为代表的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之可采性进行研究。
二、国际商事仲裁非法证据可采性的“规则缺失”
各国国内法往往通过立法或判例发展的方式对非法证据可采性问题作出较明确的规定。以美国为例,作为英美法系的代表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美国通过维克斯案(Weeks v. United States) 和马普案(Mapp v. Ohio)等判例正式确立了刑法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凡通过违反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获取的证据均不具有可采性。 5 简言之,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对象是通过非法搜查等方式获取的实物证据,该规则旨在确保执法人员在程序中合法扣押或搜查。我国目前亦在刑事案件中明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国际法通常不对证据可采性问题作出严格规定。 6 以国际法院为例,《国际法院规约》仅在第52条强调证据必须在指定期限内提交,除此之外未对证据可采性施加任何限制。概括而言,国际法院适用的证据可采性一般原则为:当事方提供的证据通常都是可采的。 7 这一原则在国际法院于其成立之初审理的科孚海峡案(Corfu Channel Case)中得到体现,并为法院在后续案件中对该问题的处理提供基础。该案源于1946年,一支英国舰队驶入科孚海峡时,引爆阿尔巴尼亚布下的水雷,从而造成英国舰队大量人员死伤。为了证明阿尔巴尼亚违反国际法上的通知义务,英国皇家海军在没有得到阿尔巴尼亚许可的情况下进入该水域扫雷,并将发现的水雷作为证据向国际法院出示。国际法院虽认定英国海军的行为侵犯了阿尔巴尼亚国家主权,是一种国际不法行为,然而法院并未对英国作出实质性惩罚判决,也并未在程序中排除英国以非法侵犯他国主权这一方式所获取的证据。 8
国际商事仲裁在处理非法证据可采性时同样面临着规则缺失的困境。一般而言,仲裁庭对证据问题的处理主要根据仲裁协议、机构仲裁规则和仲裁地法中的强制性规定。 9 在这三者中,仲裁协议中的争端解决条款很少细化到证据问题,仲裁地法的强制性规定往往涉及的是更为宏观的公共利益与政策等事项,故事实上仲裁庭主要参考仲裁规则中的证据条款。然而, 仲裁规则能给予仲裁庭的指导也十分有限。一方面,各机构仲裁规则中证据条款数量普遍较少,鲜有仲裁机构制定专门的证据规则。 10 另一方面,仲裁规则中的证据条款往往仅规定仲裁庭需要判断证据可采性,但缺少进一步指导细则。总体而言,国际商事仲裁尚未形成有关非法证据可采性的具体规则。
当然,不同于国内法院适用严格的证据规则,国际仲裁庭在证据可采性问题上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这已成为国际仲裁的共识并在多个机构规则中得到体现。 11 例如,《伦敦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第22条第1款第6项指出,“在事先给予各方当事人合理的机会以表达他们的意见的基础上,仲裁庭有权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依照仲裁庭自己的动议进行下列事项,……裁定对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任何有关事实或专家意见方面的材料的可采性、关联性和重要性,是否适用任何严格的举证规则(或其它规则)等”。
最后,仲裁庭在实践中频繁地援引《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取证规则》(IBA Rules on the Taking of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以下简称《IBA规则》)来弥补仲裁协议或机构规则中证据规则的缺失。 12 《IBA规则》旨在为国际仲裁(特别是涉及不同法律传统当事人的国际仲裁)的取证问题提供高效、经济及公平的处理方式,故尽管不具有强制的法律拘束力,国际仲裁庭多次援引该规则作为处理证据问题的依据。 13
《IBA规则》中规定证据可采性问题的主要是第9条第1款和第2款。第9条第1款赋予仲裁庭在证据可采性上享有自由裁量权,第9条第2款列举了不采纳证据的7种情况。
相较于仲裁规则,IBA 证据规则给出了更加细化的判断标准。当然,对于判断非法获取证据的可采性问题上,第9条第2款起到的帮助仍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因为:首先,第9条第2款的列举是否穷尽,尚存争议;其次,第9条第2款的用语存在模糊与不确定性,例如第9条第2款第7项规定可以排除证据的情形为“仲裁庭认定基于程序的经济性、适当性和公平的考虑,以及平等对待当事人的考虑具有说服力。”不同仲裁庭对何为程序的经济性、适当性和公平缺乏统一标准,实践中容易引发分歧;最后,第9条第2款中规定的不采纳证据的7种情形并不包括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因此即便援引《IBA规则》,仲裁庭很难直接对该问题得出结论。
三、非法证据的可采性——基于国际投资仲裁实践分析
相较于投资仲裁,商事仲裁显然具有更高的保密性,这使得通过考察商事仲裁实践来研究仲裁庭对该问题的处理路径显得几无可能。与之相反,投资仲裁的透明度使得公众能接触到大量案件材料,从而使得将投资仲裁处理该问题的经验“嫁接”于商事仲裁成为可能。考虑到投资仲裁与商事仲裁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在很多问题上具有共通性, 14 故在缺乏明确判断路径的现状下,可考虑参考投资仲裁相关案例在解决非法证据的可采性问题上的做法来解决国际商事仲裁中非法证据的可采性问题。下面对有关投资仲裁实践进行分析。
(一)决定不予采纳非法获得的证据之实践
在多个投资仲裁案件中,仲裁庭基于不同考量均拒绝采纳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
1. 梅赛尼斯诉美国案
梅赛尼斯(Methanex)诉美国是一起根据北美自由协定提起的投资仲裁。该案投资者梅赛尼斯公司是全球最大的乙醇生厂商和经销商。由于加州政府颁布了禁止使用或销售某种汽油添加剂的禁令,梅赛尼斯根据协定第11章向美国提出索赔申请。
仲裁过程中,梅赛尼斯公司对美国政府的一位证人冯德(Vind)先生的资格持疑。为了证明冯德先生与加州政府的利益关系,梅赛尼斯公司向仲裁庭提交了一系列文件,包括冯德先生的私人笔记、信函、通讯录等。对此,美国政府指出,这些文件是梅赛尼斯公司的私人侦探非法潜入冯德先生工作大楼搜寻垃圾箱而得。尽管梅赛尼斯极力主张其“垃圾搜索”行为不构成美国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取证,美国仍坚持请求仲裁庭排除这些证据。
仲裁庭主要从两方面分析了证据的可采性问题。首先,仲裁庭强调作为一般法律原则,争端当事方均有义务在仲裁程序中恪守善意原则,尊重程序公正。因此,正如同美国政府不被允许提交其依靠情报资源监视投资活动而获得的文件,梅赛尼斯通过“垃圾搜索”获得的证据也不应被采纳;其次,仲裁庭分析了该证据的重要性。在仔细考虑文件内容后,仲裁庭认定本案还有更直接的口头和书面证据能证明梅赛尼斯公司的主张,即争议文件对于本案而言并非不可或缺,对案件结果也不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上述分析,仲裁庭最终决定不采纳梅赛尼斯公司提交的证据。 15
2. 萨纳伊诉土库曼斯坦案
萨纳伊(Sanayi)诉土库曼斯坦案是一起建筑工程承包合同争端。在施工过程中,投资者土耳其萨纳伊公司与土库曼斯坦政府对合同履约情况产生分歧。根据《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双边投资协定》第7条,双方在争端产生后应尽可能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争端,若争端自被提起之日起6个月内未解决,投资者可提起仲裁申请。
为了证明自己根据投资协定第7条向土库曼斯坦国内法院寻求用尽当地救济的努力是徒劳的,萨纳伊公司向仲裁庭提交了一份从维基解密网站下载的名为《土库曼斯坦:迈向司法独立》的文件。在该文件中,土库曼斯坦承认本国国内司法体制存在弊端,“鉴于土库曼斯坦自上而下的决策形成机制,很难想象法官会仅仅根据案件事实作出裁判,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利益的案件中。同时,政府权力扩张和腐败受贿的情况也不容忽视……” 16 土库曼斯坦政府认为维基解密网站从事的是非法获取文件行为,故申请方提交的证据不应被采纳。
仲裁庭并未直接回应维基解密文件的可采性,而是用较长的篇幅分析这份文件与投资者主张间的相关性。仲裁庭认为,作为一份内容广泛的第三方研究报告,该文件仅概括性指出土库曼斯坦国内司法体系缺乏独立、 对土耳其投资者并不友好的情况,但这并不能必然地证明 萨纳伊公司的主张。相反, 萨纳伊公司必须明确地向仲裁庭展示其诉诸土库曼斯坦国内法院的经过,才能分析出其寻求东道国当地救济的权利是否被剥夺。因此,仲裁庭认定萨纳伊公司所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主张,故不予采纳。 17
3. 伊迪夫诉罗马尼亚案
伊迪夫(EDF)诉罗马尼亚案涉及通过窃听获得的录音文件的可采性。本案申请方伊迪夫公司声称由于拒绝向时任罗马尼亚首相行贿,其在罗马尼亚境内的投资遭到了政府阻挠。伊迪夫公司向仲裁庭提交了一份录音文件,内容为罗马尼亚政府官员对其提出了必须行贿才能继续开展业务的要求。罗马尼亚请求仲裁庭拒绝采纳该证据,并提出三点理由:首先,伊迪夫公司早在7年前就录下了对话,但直到7年后才将该证据公布,这种行为有违善意原则;其次,该录音是伊迪夫公司在另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下非法佩戴窃听器录制,该取证方式侵犯当事人隐私权;再次,录音文件应提供原件,伊迪夫提供的录音真实性、完整性存疑。
仲裁庭针对这三点理由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首先,仲裁庭指出,考虑是否采纳证据的标准之一是证据的可靠性和真实性,采纳一份无法辨明真假的文件无疑是浪费时间。鉴于该录音大量对话内容缺失,且很有可能进行了内容增删等操作,该录音内容不具有可靠性与真实性。随后,仲裁庭重点分析了非法窃听这一取证行为。仲裁庭参考了科孚海峡案,认为非法取证的后果应加以个案分析。同时,仲裁庭赞同梅赛尼斯案对非法取证效力的分析,指出善意参与程序的重要性。鉴于该录音是在伊科布(Iacob)女士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录,这显然侵犯了其隐私权,采纳这份证据将有违国际仲裁中的善意原则和公平原则。最后,仲裁庭分析了伊迪夫公司直到7年后才公布该证据这一行为。仲裁庭结合双方证言,认定EDF公司早在7年前已掌握该录音,这种无理由的故意迟延提交显示了伊迪夫公司的非善意。 18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涉及投资者对东道国的腐败指控,鉴于索贿指控的严重性,仲裁庭在本案采取“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明标准。 19 这也不难理解为何仲裁庭在基于上述分析的前提下,最终决定不采纳该份录音文件。
4. 利班纳科诉土耳其案
本案涉及土耳其政府通过非法监听方式获得的与投资者有关的信息的可采性问题。塞浦路斯公司利班纳科(Libananco)指责土耳其政府通过非法监听获取了大量有关本案的机密文件。土耳其政府承认存在监听行为,但表示只是为了调查另一起洗钱案,与本案无关。
仲裁庭首先指出,本案双方在证据问题上的分歧恰恰揭示了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以下简称ICSID)仲裁中的一些核心问题,如基本的程序公正,对法律特权和保密信息的尊重,赋予双方寻求意见以及自由、不受干涉地推动案件进程的权利等等。仲裁庭继而强调,当事方均应公平善意地参与仲裁过程,这一原则适用于包括国际投资仲裁在内的所有仲裁。对于土耳其提出的调查洗钱犯罪这一抗辩理由,仲裁庭表示其无意否认一个主权国家享有追踪犯罪的天然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权力的行使不受约束,也不代表一个国家可以通过阻碍ICSID仲裁开展的方式进行犯罪调查。最后,仲裁庭再次强调了法律特权和保密制度的重要性,并认为采纳这些证据将会对利班纳科公司造成程序偏见。 20
(二)决定采纳非法获得的证据之实践
当然,在个别案件中,仲裁庭决定采纳当事方提交的涉及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其中以尤科斯(Yukos)诉俄罗斯案和卡拉图布(Caratube)诉哈萨克斯坦案最为典型。
1. 尤科斯诉俄罗斯案
作为国际投资仲裁里程碑式案例,尤科斯诉俄罗斯案同样涉及了维基解密文件作为证据的可采性问题。
本案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作为尤科斯税务审计公司的普华永道为何撤回其近10年来对尤科斯的全部审计报告。尤科斯指出,普华永道之举并非因为尤科斯管理层提交的财务报告不正确,而是迫于俄罗斯政府向其施加的政治压力。为了证明俄罗斯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是一场“政治运动”,尤科斯提交了一系列公布在维基解密网站上的美国大使馆和普华永道之间的电文作为证据。
仲裁庭在裁决中指出,电文中审计员向美国大使馆的坦诚陈述证明了其确实面临着来自俄罗斯的压力:普华永道很担心自己与俄政府的关系趋向紧张,并担心因本案失去其在俄罗斯的营业资格和业务。普华永道认为尤科斯案本质是政治势力的对抗,并承认自己撤回审计意见与俄罗斯向其施加的压力间存有联系。 21
同萨纳伊诉土库曼斯坦案相同,本案仲裁庭亦未对非法证据本身的可采性给出明确回应。但鉴于仲裁庭在裁决中至少有 20 处引用了维基解密文件作为证据进行论证,可以说仲裁庭在事实上采纳了该文件。因此,一些评论者认为,尤科斯案裁决透露出在国际投资仲裁中,非法获取的证据具有可采性这一信号。22
2. 卡拉图布诉哈萨克斯坦案
卡拉图布诉哈萨克斯坦案是另外一起在ICSID下提起的投资仲裁,本案主要涉及投资者从非法网站上自行下载的文件的可采性问题。
仲裁进程中,卡拉图布公司提交了从名为“哈萨克解密”(KazakhLeaks)的网站上下载的11份文件作为证据。“哈萨克解密”是由黑客建立的一个信息分享网站,通过入侵哈萨克斯坦政府网络系统,黑客在该网站上传了约6万份政府文件。哈萨克斯坦强烈反对申请方提交该证据,并请求仲裁庭将这些“被盗文件”排除出仲裁程序。双方均就该证据的可采性问题提交了法律意见。 23
仲裁庭认为,在证据问题上,法律特权的保护应始终放在首位。因此,仲裁庭并未采纳4份涉及律师客户间通信的文件,但采纳了卡拉图布公司提交的其他不涉及法律特权的文件作为证据。 24
本案仲裁庭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以下两点思考。首先,涉及法律特权的信息不应作为证据被提交。在这一点上,仲裁庭充分尊重了《IBA规则》第9条第2款关于法律特权的规定。其次,本案仲裁庭似乎释放出,除特权信息外,非法取得的证据原则上可以被采纳的信号。
四、仲裁庭决定非法证据可采性的考量因素
由于仲裁规则普遍未对证据可采性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国际投资仲裁实践呈现出个案裁判,缺乏统一标准之局面。不过通过对已有案例的梳理,仍能提取出某些共通的考虑因素:首先,从证据本身而言, 仲裁员会关注证据内容是否具有真实性,与案件是否具有相关性,对结果是否产生重要性。其次,仲裁庭会关注采纳这份证据对于程序公平正义是否产生影响。再次,仲裁庭还会关注证据是否涉及保密信息、律师—当事人信息等为法律特权所包含的内容。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判断非法证据的可采性同样要考虑这些因素,因此投资仲裁对该问题的分析路径对于商事仲裁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一)非法证据的重要性及其与案件的相关性
证据应该与案件具有相关性,并对案件结果有重要影响。一般认为,相关性要求证据有助于当事方展示案情、证成主张,重要性侧重证据有助于仲裁庭发现案件真相或作出裁决。 25 由于仲裁一裁终局的属性,仲裁庭往往倾向采纳而非排除证据来帮助发现案件真相,但这并非意味着当事方提交的任何证据均应被采纳。国际仲裁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国内法中的某些证据排除规则。 26 对于仲裁庭而言,若一份待提交的证据于案件不相关不重要,而该证据又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得,采纳该证据显然得不偿失。
梅赛尼斯案即引入证据相关性、重要性标准来帮助判断可采性问题。仲裁庭认为,鉴于争议文件不能达到申请方梅赛尼斯公司预期的证明效果,该证据对案件结果不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决定不采纳该证据。同样,在萨纳伊诉土库曼斯坦案中,仲裁庭重点论述了提交的维基解密文件与试图证明的诉求间并不相关,因此拒绝采纳。相反,在尤科斯案中,尽管仲裁裁决在维基解密文件是否可被采纳为证据上保持缄默,但基于文件泄露的信息直接涉及本案争端,仲裁庭在裁决书论理部分大量引用了维基解密文件的内容,事实上承认了其可采性。
在笔者看来,国际商事仲裁庭在衡量非法取得的证据可采性时,可先考虑该证据的相关性、重要性问题。若仲裁庭不认为证据与争端有联系,可直接决定不予采纳该证据。相反,若该证据与案件相关或对案件结果产生重要影响,仲裁庭可认定证据具有初步(prima facie)可采性,并结合其他标准作出进一步认定。
(二)非法证据的真实性
证据应具有真实性、可靠性。两大法系虽对证据种类各有侧重,但均出于对证据真实性的考量。英美法系重视收集证人证言,并通过交叉询问来确保口头证词的真实性;大陆法系则普遍认为由于争端往往在瞬间发生且证人的事后回忆存有偏差,从而使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大打折扣,故倾向书面证据。 27 当今,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对文件原件的修改或伪造变得能更加容易,这也使得判断证据的真实性显得尤为重要对仲裁庭而言,采纳一份内容上不具有真实性、可靠性的证据将会使依靠该证据作出的裁决面临着被撤销的风险。
黎巴嫩国内仲裁庭在其2015年作出的一份决定中指出,当事方若想使用维基解密文件作为证据,必须确保其内容的真实性或提供其他证据来印证文件所含信息的准确性。类似的,在伊迪夫诉罗马尼亚案中,仲裁庭指出,判断录音文件的真实性是决定是否采纳该文件的前提。由于本案申请方提交的录音文件缺失了开头与结尾,内容不完整,录音中存在多达20处停顿等,仲裁庭认定该录音的真实性存疑,并以此作为拒绝采纳该证据的理由之一。
笔者认为,在判断非法证据可采性之前,仲裁庭可自行对非法获取的证据内容是否真实作出判断。与相关性和重要性的判断相同,若仲裁庭不认定证据具有真实性、可靠性,可直接决定不予采纳该证据。相反,若仲裁庭确信证据的真实性,可认定证据具有初步(prima facie)可采性,并结合其他标准作进一步认定。
(三)提交非法证据的一方是否亲自参与了非法取证
作为起源于英美衡平法中的一项法律原则,“干净之手”强调寻求救济或主张权利的一方必须清白无暇。28 尽管在尤科斯案中,仲裁庭明确指出“干净之手”原则并非联合国《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第3项所规定的一般法律原则, 29 但仲裁庭可以将其与善意原则、程序正当原则等挂钩而使其得到适用。 30 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干净之手”原则在处理争端方违法行为时,包括非法取证这一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31
在梅赛尼斯诉美国案中,仲裁庭将梅赛尼斯公司亲自参与了“垃圾搜索”这一非法的证据获取过程作为认定证据不具有可采性的理由之一。在伊迪夫诉罗马尼亚案中,仲裁庭将投资者携带录音器偷录谈话内容这一行为视为违反了“干净之手”原则,作为不采纳证据的理由之一。在利班纳科诉土耳其案中,利班纳科在书面陈述中着重强调了土耳其政府以监听的方式获取文件的行为违反了“干净之手”原则,故不应采纳土耳其政府提交地证据。此外,欧盟法院在波斯银行诉欧洲理事会一案中的意见也颇具参考价值,该案同样涉及一份维基解密文件能否被采纳为证据这一问题。法院认为,维基解密文件的泄漏渠道在源头上或许违法,但试图提交该文件作为证据的波斯银行并未参与非法获取过程。证据源头潜在的非法性不应成为阻碍案件一方提交该证据的理由。 32
因此,笔者认为,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判断非法证据的可采性问题上,仲裁庭可以引入“干净之手”原则,即提交非法获取的证据而使自己在案件中获益的争端当事方若亲自参与了非法取证过程,该证据可被认定不具有可采性。 33
(四)非法证据是否涉及法律特权
是否涉及法律特权是仲裁庭在判断证据可采性时的另一个参考因素。所谓法律特权,是指被法律认可的拒绝向法庭或另一方当事人出示证据的权利。 34 对于法律特权,两大法系有着不同的理解。英美法系对特权概念持广义解释态度,并将其与保密制度加以区分。大陆法系虽并未有特权概念,但也要求程序参与方恪守保密性。 35 目前国际仲裁中比较普遍的几种特权包括律师客户特权制度、商业秘密特权保护制度、公共特权制度等。 36 国际投资仲裁虽缺乏成文的“特权规则”,但在实践中已经在适用“特权规则”上形成一些共识。 37
因此,仲裁庭如果认定当事方提交的非法取得的证据中涉及侵犯法律特权,可不采纳该证据。在利班纳科诉土耳其案中,仲裁庭指出,法律特权与机密信息的保护应受到高度重视。如果允许一方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取特权与机密信息并使自己在案件中受益,将对另一方造成严重的偏见。同样,在卡拉图布诉哈萨克斯坦案中,仲裁庭将投资者与其律师之间的邮件信函以侵犯法律特权与违反机密信息的保护为由排除,而允许提交其他不涉及侵犯法律特权的证据。
当然,界定证据内容是否涉及法律特权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IBA规则》第9条第2款第2项规定,如果一项证据的出示会造成法律障碍或形成法律特权,仲裁庭可以排除该证据。第9条第3款列举了判断何为法律障碍或特权时可以考虑的五点因素,其中第1项项为“与提供或获得法律建议有关、或者出于提供或获得法律建议的目的而产生的文件材料、陈述和口头沟通”。从这个角度出发,尽管律师客户特权制度已被公认为是一种法律特权,但需要注意的是并非律师与其客户之间的所有沟通文件均可受到特权制度的保护。正如仲裁庭在维托·加洛(Vito G. Gallo)诉加拿大一案中指出,只有当律师是以专业律师身份(而非其他身份)给出相关意见,客户和律师之间存在信任关系,文件材料是因出于提供或获得法律建议之目的而制作,并且双方均合理期待即便产生相关争议该信息将被保密时,律师与客户特权制度方可得以适用。 38
五、借鉴与展望
由于国际投资仲裁的仲裁庭享有的高度自由裁量权,目前的投资仲裁实践尚未对判断非法证据的可采性形成统一的标准。在笔者看来,未来非法证据的可采性问题仍将保持一定的复杂性,仲裁实践对该问题的判断也可能存在不同,不同仲裁庭依旧倾向于从个案案情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此外,鉴于来自不同法律背景和文化的仲裁员对这证据问题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力求国际投资仲裁在判断非法获取证据的可采性时得出统一结论尚显不切实际。当然,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即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必然被排除。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亦是如此。
在具体的判断路径上,参考已有规则和有关国际投资仲裁案例判例,笔者认为,在判断国际商事仲裁非法证据的可采性问题上,以下的方法或许可供参考:首先,仲裁庭可以考虑该证据的相关性、重要性问题。若仲裁庭不认为证据与案件有联系,可直接决定不予采纳该证据。相反,若该证据与案件相关或对案件结果产生重要影响,仲裁庭可认定证据具有初步可采性;其次,仲裁庭可对非法获取的证据内容是否真实作出判断。若仲裁庭不认为证据具有真实性、可靠性,可直接决定不予采纳该证据。相反,若仲裁庭确信证据的真实性,可结合其他标准作出下一步的判断;再次,仲裁庭可以引入“干净之手”原则,即若争端当事方亲自参与了非法取证过程或采纳该证据会使另一方的程序利益受损,该证据可被认定不具有可采性;最后,仲裁庭可以判断提交的证据是否受证据特权的保护,如果相关信息受到证据特权制度的保护,则仲裁庭可认定不予采纳该证据。
注释:
* 金挺峰,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助理。本文原载《仲裁与法律》第147期。
1.Samira A. Saleh, “Reflections on Admissibility of Evidence: Interrelation Between Domestic Law and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15, 1999, p.142.
2.[英]艾伦·雷德芬等:《国际商事仲裁法律与实践》,宋连斌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7页。
3.“Verdict in Bradley Manning case”,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special/national/manning-verdict/, July 8, 2019.
4.“Gillard refines verdict on Assange”, http://www.abc.net.au/worldtoday/2010/s308673.htm, July 8, 2019.
5.《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人民保护其身体、住宅、文件与财产之权利,以对抗无理由之搜查和扣押,不得被侵犯。除有合理根据并宣誓保证,并详述搜查之地点、须扣押之人或物之外,不得颁发搜捕证。”
6.Charles N. Brower, “Evidence befor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The Need for Some Standard Rules”, The International Layer 28, 1994, p.47.
7.张卫彬:《国际法院解决领土争端中的证据问题研究》,华东政法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第68页。
8.Corfu Channel case, Judgment of 9 April 1949, I. C. J. Reports 1949, p. 35.
9.Marghitola Reto, Document Production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Netherla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5, p.122.
10.以目前在国际社会认可度较高的仲裁规则为例,2013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仅有第20条一个条文规定证据问题,2018年《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机构仲裁规则》同样仅有第22条一个条文涉及证据问题。当然,个别仲裁机构可能在仲裁规则之外另行制定专门的证据规则或证据指引,例如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自2015年起施行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证据指引》。该指引第19条规定以下两类证据不具有可采性,即仲裁庭认为不应被采纳的证据,尤其是那些律师与客户之间的保密通讯或涉及当事人之间和解谈判的证据,以及仅在调解程序中披露的证据和信息。但对于非法证据的可采性问题,该指引同样没有作出规定。
11.Nathan D. O’Malley, Rules of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 Annotated Guide, London, Informa Law International,2012, p.267.
12.Jeffrey Waincymer, Procedure and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Netherla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2, pp.750-751.
13.Cambodia Power Company v. Kingdom of Cambodia, ICSID Case No. ARB/09/18, Amended Decision on the Claimant’s Application to Exclude Mr Lobit’s Witness Statement and Derivative Evidence, 14 February 2012, p. 2; Tidewater Inc., Tidewater Investment SRL, Tidewater Caribe, C.A., et at. v. The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ICSID Case No. ARB/10/5, Procedure Order No.1 on Production of Documents, 29 March 2011, para. 6; CME Czech Republic B.V. v. The Czech Republic, UNCITRAL, Partial Award, 13 September 2001, para. 46.
14.关于投资仲裁与商事仲裁的共同性,参见傅攀峰:《商事仲裁与投资仲裁:当今两者差异几何?》载《仲裁研究》2014年第2期。
15.Methanex Corporation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NCITRAL, Final Award, Part II-Chapter I, 3 August 2005, paras. 54-59.
16.Kılıç İnşaat İthalat İhracat Sanayi v. Turkmenistan, ICSID Case No. ARB/10/1, Award, 2 July 2013, p. 58, para. 4.3.16.
17.Ibid, para. 8.1.10.
18.EDF v. Republic of Turkey, ICSID Case No. ARB/05/13, Procedural Order No. 3, 29 August 2008, paras. 29-46.
19.Ibid, para. 30.
20.Libananco Holdings Co. Limited v. Republic of Turkey, ICSID Case No. ARB/06/8, Decision on Preliminary Issues, 23 June 2008, paras. 78-80.
21.Hulley Enterprises Ltd. v. Russian Federation, PCA Case No. AA 226, Award, 18 July 2014, para. 1218.
22.Cherie Blair and Ema Vidak Gojkovic´, “Wikileaks and Beyond: Discerning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the Admissibility of Illegally Obtained Evidence”, ICSID Review 33, 2018, pp.235–259.
23.Caratube International Oil Company LLP and Mr. Devincci Saleh Hourani v. Republic of Kazakhstan, ICSID Case No. ARB/13/13, Award, 27 September 2017, paras. 150&152.
24.Ibid, para. 1259.
25.Konstantin Pilkov,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riteria for Admission and Evaluation”, Arbitration 80, 2014, pp. 148-149.
26.Richard Mosk, “The Role of Facts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Recueil Des Cours 304, 2003, p.120.
27.Josefa Sicard-Mirabal and Yves Derains, Introduction to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Netherla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8, p. 194.
28.Patrick Dumberry, “State of Confusion: The Doctrine of ‘Clean Hands’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fter the Yukos Award”,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s and Trade 17, 2016, p.230.
29.Hulley Enterprises Ltd. v. Russian Federation, PCA Case No. AA 226, Award, 18 July 2014, para.1358.
30.例如在Inceysa诉El Salvador一案中,仲裁庭虽未直接适用“干净之手”原则,但仍强调没有任何一个基于理性的法律体系会允许实施违法行为的一方从中受益,Inceysa Vallisoletana S.L. v. Republic of El Salvador, ICSID Case No. ARB/03/26, Award, 2 August 2006, para.244.
31.Aloysius Llamzon, “The State of the “Unclean Hands” Doctrin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Yukos as Both Omega and Alpha”, ICSID Review 30, 2015, pp.315-325.
32.Persia International Bank v Council, Case T-493/10, ECLI:EU:T:2013:398, para. 95.
33.Nikki O’Sullivan, “Lagging behind: is there a clear set of rules for the treatment of illegally obtained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s?” http://arbitrationblog.practicallaw.com, July 8, 2019.
34.Norah Gallagher, “Legal Privileg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Review 2, 2003, p. 45.
35.Tom Ginsburg and Richard Mosk, “Evidentiary Privilege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50, 2013, pp.345-346.
36.崔起凡:《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证据问题研究》,华东政法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第142页。
37.C. Tevendale and U. Cartwright-Finch, “Privileg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s It Time to Recognized the Consensu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6, 2009, pp.823, 839.
38.Vito G. Gallo v. Government of Canada, NAFTA/UNCITRAL/PCA, Procedural Order No. 3, 8 April 2009, para. 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