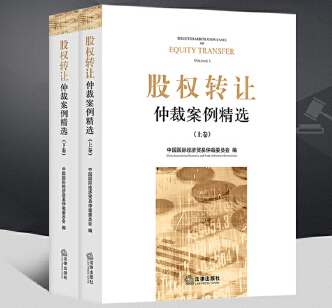
【关键词】投资融资型股权转让 对赌协议 股份回购 实际履行
【焦点问题】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业绩承诺和现金补偿条款”及“股份回购条款”是否有效?在“对赌”中该两个条款项下之请求是否都应支持?认定有效的“对赌协议”是否具备可执行性?
【焦点评析】
本案的基本案情是,投资方(即本案“申请人”,以下同)为向目标公司(即本案“第二申请人”,以下同)投资,与目标公司及其原股东(即本案“第一申请人”,以下同)共同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和《增资扩股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在《增资协议》中约定了投资方以溢价增资方式入股目标公司的价格、获得股权比例、交割等事项,在《补充协议》中特别约定了“业绩承诺和现金补偿条款”和“股权回购条款”,如目标公司未达到约定的净利润指标,则原股东向投资方给予现金补偿,并对现金补偿的计算方法等做了详细约定;如果目标公司在目标上市日期之前未能成功上市,则投资方有权要求原股东或目标公司按约定的回购价格回购其持有的目标公司全部或部分股份,且原股东和目标公司之间对履行股权回购义务互相承担连带责任。上述两协议签订后,投资方按约定支付了全部增资款,并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获得股东地位,但目标公司连续三年的实际净利润指标均未能达到业绩承诺指标,也未能在目标上市日期之前成功上市,投资方向原股东及目标公司发函要求支付未达承诺业绩的现金补偿款、履行股权回购义务并支付股权回购款未果,遂提起本案仲裁,请求仲裁庭裁决原股东支付现金补偿款,履行股权回购义务,支付股权回购款;请求目标公司对原股东的股权回购义务及违约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现结合本案案情及法律适用焦点问题,评述如下:
一、“对赌协议”纠纷的特殊性
近年来我国股权转让纠纷中频繁发生的争议是有关“对赌协议”的纠纷,由于“对赌协议”(“Valuation Adjustment Mechanism”中文翻译为“估值调整机制”)的交易思路来自于西方投资领域中的投资方和融资方之间的商业利益博弈,也是投资方控制投资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一种交易模式,在我国的民商事活动中属于“舶来品”。相应地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都没有相对应的明确法律界定,导致近年来出现的此类纠纷在法律适用、“对赌协议”的有效性和可执行性方面突出表现出其区别于其他股权转让纠纷的特殊性。
(一)“对赌协议”的法律适用范围及法律形式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中的解释:“实践中俗称的‘对赌协议’,又称估值调整协议,是指投资方与融资方在达成股权性融资协议时,为解决交易双方对目标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成本而设计的包含了股权回购、金钱补偿等对未来目标公司的估值进行调整的协议。”这个解释揭示了实践中“对赌协议”包含的两个基本经济行为:一个是投资方与融资方之间的股权融资行为;一个是交易双方对目标公司的估值进行调整的行为。因此,对应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上述两种经济行为都应属于民商事法律调整的范畴,具体适用的法律应包括《合同法》、《公司法》、外商投资企业相关法律、法规等。对此,《九民纪要》中也明确提出:“人民法院在审理‘对赌协议’纠纷案件时,不仅应当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还应当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实践中,“估值调整协议”的法律实现方式通常是以《公司法》中的“增资”和“股权转让”的法律内涵来加以适用,以“增资协议”的形式来确立投资方与融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以“股权转让协议”的形式来实现估值调整的结果。
本案中涉及的协议除了《增资协议》之外还有一个《补充协议》,《增资协议》中并不涉及“对赌条款”,而在《补充协议》中约定了“现金补偿”条款和“股权回购”条款。这种将“对赌”交易安排分为两个协议的方式也是目前实践中比较常见的做法。但采用分开两个协议的形式并未改变其经济行为的本质和一致性,即两个协议的内容合并在一起才完整地建立了投资方与融资方之间的包含“对赌”条件的股权投资法律关系。本案仲裁庭在论述这两个协议之间的关系时也肯定了这一点,认为:《增资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缔约目的有所不同,《增资协议》的缔约目的在于使得投资方取得目标公司的股份,《补充协议》的缔约目的则在于使得投资方退出目标公司,以及获得原股东、目标公司提供的现金补偿等。履行《补充协议》系以《增资协议》履行完毕作为基础或者前提,投资方仅在依照《增资协议》持有目标公司的股份后,才能在满足《补充协议》约定的条件时退出目标公司或者获得现金补偿。
“对赌协议”的法律适用范围问题目前并未成为此类纠纷案件的焦点,但从最高人民法院的“海富案” 1 中,可以发现针对同一案件事实,法律适用的不同导致审判结果的重大差异:一审法院认定“业绩补偿条款”的法律效力问题时适用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8条 2 关于企业利润根据合营各方注册资本的比例进行分配的规定,从而认定该条款属于《合同法》第52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无效合同情形;二审法院同样认定该条款属于《合同法》第52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无效合同情形,但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4条第2项 3 之规定,认为“业绩补偿条款”违反了投资领域风险共担的原则,使得投资方不论目标公司经营业绩如何,均能取得约定收益而不承担任何风险,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最高人民法院支持了一审法院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8条的法律适用,否定了二审法院“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法律适用,认为二审法院认定投资方的投资“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判决返还投资款没有法律依据。
个人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发布于1990年,对于规范彼时的经济活动具有司法审判的指导意义。对于近年来我国的投资领域中大量出现的新的“对赌”形式的交易活动,是否可以适用“过时”的但未废止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尚存疑。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所称“二审法院认定投资方的投资‘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判决返还投资款没有法律依据”的结论本身亦没有给出法律依据。基于“新法优于旧法”的法律适用原则,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的《外商投资法》废止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并明确外商投资企业的组织形式、组织机构及其活动准则适用《公司法》 4 ,而根据2018年修正的《公司法》第34条 5 的规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红并非必然违反法律规定。因此,今后在认定类似“海富案”情形下的“对赌条款”的效力时,应谨慎判断哪些规定属于《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强制性规定”,只有违反“强制性规定”才会导致合同无效。
(二)“对赌协议”的法律效力及履行“对赌”义务的主体
目前,在涉及“对赌协议”的纠纷案件中,焦点问题是“对赌协议”或含有“对赌条款”的增资协议的有效性,以及履行“对赌”义务的主体问题。从现有的生效法院判决及《九民纪要》的观点来看,形成的一个基本判断思路是区分不同主体之间的“对赌”,协议的有效性根据主体不同而有所不同。主要观点总结归纳如下:
1、投资方与股东之间的“对赌条款”有效。此类观点比较典型的判例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海富案”、“蓝泽桥案” 6 ,江苏省高院的“刘来宝与阮荣林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 7 、“江苏华工案” 8 。这些案例认定投资方与股东之间的“对赌条款”有效的核心裁判基准是维护市场主体的意思自治、认定无效合同的“法定主义”原则,即严格按照《合同法》第52条 9 规定的五种合同无效的情形为认定标准,未出现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的,不轻易认定合同无效。这一观点,在《九民纪要》中也得到确认,即:对于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订立的“对赌协议”,如无其他无效事由 10 ,认定有效。
2、投资方与目标公司之间的“对赌条款”无效。对于投资方与目标公司之间的“对赌条款”的效力问题,目前出现的案例显示存在不同的观点,落脚点聚焦在该等条款是否存在损害目标公司及其债权人利益的判断上。如“海富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定该条款无效的主要理由是:该条款使得投资方可以在目标公司中取得相对固定的收益,脱离了目标公司的经营业绩,损害了公司利益和公司债权人利益,违反《公司法》第20条 11 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8条 12 的规定。而在“江苏华工案”中,江苏高院则认为协议内容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约定的固定收益不存在脱离目标公司正常经营所应负担的经营成本及所能获得的经营业绩的企业正常经营规律,目标公司在履行法定程序后回购本公司股份,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及债权人利益,亦不会构成对公司资本维持原则的违反,从而认定了投资方与目标公司之间的“对赌条款”有效。这两个判决关于“对赌条款”中涉及的“固定收益”约定的判决观点差异较大:“海富案”认为固定收益的约定脱离了公司的经营业绩,从而损害了公司和债权人的利益;“江苏华工案”不是从固定收益的约定本身判断是否构成损害公司和债权人的利益,而是从约定的固定收益回报率不明显过高的事实得出不存在脱离公司正常经营业绩的结论。
追根溯源,关于“固定回报”的说法应源于原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法以及外债政策方面的一些通知文件 13 中,其基本观点是:对外资方承诺“固定回报”,违反中外投资者“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共负亏损”的原则;保证外方“固定回报”,相当于变相“对外举债”,即“固定回报”使得外方成为收取固定“利息”的借款者,而非真正的投资者。随着这些法律、法规和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固定回报”的违法、违规特性逐渐模糊,再加之法定的无效合同中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理论上还有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或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之分,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不导致合同或条款的无效之说,因此,仅以存在“固定收益”条款为由认定“对赌协议(条款)”无效也似乎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商事活动及相关法律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对此,《九民纪要》采取了“就事论事”的务实态度,即:“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订立的‘对赌协议’在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的情况下,目标公司仅以存在股权回购或者金钱补偿约定为由,主张‘对赌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3、目标公司对投资方与股东的“对赌条款”承担连带责任的条款的有效性问题,如果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对合同无效的判定严格遵循“法定主义”的原则来考量,目标公司对投资方与股东的“对赌条款”承担连带责任的条款则应以有效为原则,以无效为例外。但从目前的案例来看,既有认定为无效的案例,如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天津雷石案” 14 ,以目标公司为股东的回购义务向投资方承担连带责任的约定会使投资方取得固定收益、脱离了目标公司的经营业绩、损害公司及债权人利益为裁判原则认定该等条款无效;也有认定为有效的案例,如最高人民法院的“瀚霖案” 15 ,理由是合同无效的判定严格遵循法定主义,且投资方股东已对目标公司提供担保经过股东会决议尽到审慎注意和形式审查义务,其投资全部用于公司经营发展,目标公司全体股东因而受益,故应当承担担保责任。而“通联资本案” 16 的判决结果虽认定“连带责任条款”无效,但认定其无效的理由并非基于“固定收益”因素或“法定无效原则”,而是从公司治理规则的角度认定投资方、股东及目标公司均未能尽责履行股东会审慎注意义务导致担保条款无效。
综上,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就目标公司对“对赌条款”的连带责任条款效力形成的裁判规则是:连带担保责任条款的效力认定应严格遵循法定主义;在担保事项经过目标公司股东会决议尽到审慎注意和形式审查义务的情况下,连带担保责任条款合法有效,目标公司应依据担保条款承担连带责任;否则,担保条款无效。
本案中,关于投资方与原股东之间约定的“现金补偿条款”、“股份回购条款”以及目标公司对原股东就“股份回购条款”的连带责任的约定,仲裁庭遵循了合同无效的“法定主义原则”,未否定该等条款本身的有效性。但仲裁庭对于“现金补偿条款”和“股份回购条款”是否可以同时并用的问题上,从尊重“对赌”交易的实质出发,提出了新的视角。仲裁庭认为,业绩补偿属于《补充协议》股东身份继续存在情况下的履行协议行为,实质上是根据目标公司实际实现利润与预期承诺利润之偏差程度而对其当初投资入股的价格进行调整,以确保实现合理的投资条件并继续作为股东。投资方要求回购股权并支付回购款,是投资方要求退还所持有的目标公司的股份,不再拥有股东身份,其实质相当于解除《补充协议》,而且回购价格计算时已经包含全部投资资金的合理成本,若在回购同时再给予业绩补偿,在经济利益上构成不应有的重叠保障和利益。
二、“对赌协议”的实际履行及可执行性
在针对此类新经济形态下出现的“对赌协议”的无效认定问题上,从上述案例中可以看出认定标准的考量已经超出了《合同法》的范畴,如果说《合同法》第52条的认定标准是从合同行为的目的、期待的合同结果角度出发,那么上述案例中显示出来的视角则侧重于区分合同主体的差异及合同义务实际履行的可行性差异,尽管这种区分本身并没有法理基础。目前,基于《九民纪要》确立的裁判规则是,对于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订立的“对赌协议”,如无其他无效事由 17 ,认定有效并支持实际履行;对于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订立的“对赌协议”是否有效以及能否实际履行,按不同情况进行处理:(1)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订立的“对赌协议”在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的情况下,目标公司仅以存在股权回购或者金钱补偿约定为由,主张“对赌协议”无效的,不予支持,但投资方主张实际履行的,应当审查是否符合公司法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及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判断;(2)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或者第142条关于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审查,如目标公司未完成减资程序的,应当驳回;(3)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承担金钱补偿义务的,应当依据《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和第166条关于利润分配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审查,如目标公司没有利润或者虽有利润但不足以补偿投资方的,应当驳回或者部分支持,待目标公司有利润时,投资方还可以依据该事实另行提起诉讼。
由此可见,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订立的“对赌协议”即使有效,其合同是否能够得到实际履行须结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判断。而这样的裁判规则下,可能带来的是“对赌协议”有效,但继续履行合同无果的局面。因为,在以股权回购为“对赌”条件的情况下,“对赌协议”的实际履行涉及到减资程序、股权转让行为、股权变更登记程序等,而该等必要法律程序的履行取决于股东及目标公司能否履行相应的配合义务,而判决或裁决只定性,不涉及判决或裁决结果的“可执行性”,即如果得不到股东及目标公司的配合,该等判决或裁决可能会因“执行标的不明确”、“没有给付内容”等理由难以通过“强制执行”司法程序得到执行。
以金钱补偿为“对赌”条件的情况下,“对赌协议”的实际履行由于需要考量目标公司履行赔偿义务时点的实际利润情况,而通常情况下,之所以触发了“对赌”条件往往是目标公司经营业绩持续未达到承诺业绩标准的情况,金钱补偿的“对赌”条款虽然被认定有效,但如果目标公司没有利润或者虽有利润但不足以补偿投资方,“对赌”条款有效的判决或裁决也仍然不具有“可执行性”。
本案中,仲裁庭就“股份回购”条款的可执行性问题的处理没有留“尾巴”,在认定“股份回购”条款有效的基础上,裁决原股东直接向投资方支付股权回购价款及违约金,而不是裁决“履行回购义务”;同时,针对投资方提出的“履行回购义务”的抽象仲裁请求,仲裁庭又做出了进一步解释:其实质含义是将投资方持有的目标公司股份变更给原股东,说明投资方自愿在收到股权回购价款和违约金后放弃该等股份。仲裁庭认为,申请人的该等表示是合理的,应当予以尊重,但不属于仲裁庭的裁判事项,本裁决书不予裁断。这样一来,本案的涉案当事人各方实际执行仲裁裁决就具有清晰的指向,即原股东向投资方支付回购价款及违约金,投资方在收到该等款项后放弃其持有的目标公司的股份。从而力争最大限度地防止陷入裁决的不可执行局面,也避免出现仲裁裁决超裁之嫌。
【结语】
由于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于“对赌协议”纠纷的裁判规则的特殊性,应特别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分清履行“对赌”义务的主体,二是注意是否具备可执行性。分清履行“对赌”义务的主体,需要在订立“对赌协议”时界定投资方与原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全体股东、目标公司之间的“对赌”内容,从而避免“对赌协议”无效。注意“对赌协议”的可执行性,要避免陷入“合同有效,继续履行无果”的局面,可以将“对赌协议”的“履行方式”包括相关程序事项等作为协议各方应履行的义务明确列入协议条款,投资方在提起诉讼或仲裁时,“履行方式”可以作为诉讼或仲裁请求的一部分,在得到“对赌协议”有效的判决或裁决基础上,“对赌协议”的可执行问题亦有望得以一并解决。
本案的裁决思路,是在现行法律法规对“对赌协议”尚无确定的法律涵义、司法实践中尚存异议的现实情况下,本着尊重交易实质的务实态度所做的一种尝试,希望以此案例获得各界的检验、批评。
(案例评析人:杨育红)
注释:
1.最高人民法院就“苏州工业园区海富投资有限公司与甘肃世恒有色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香港迪亚有限公司、陆波增资纠纷案”再审判决([2012]民提字第11号)。
2.第8条 合营企业获得的毛利润,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法规定缴纳合营企业所得税后,扣除合营企业章程规定的储备基金、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企业发展基金,净利润根据合营各方注册资本的比例进行分配。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4条第2项 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的,是明为联营,实为借贷,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确认合同无效。
4.《外商投资法》第31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组织形式、组织机构及其活动准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等法律的规定。
5.《公司法》第34条 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
6.最高人民法院就“蓝泽桥、宜都天峡特种渔业有限公司、湖北天峡鲟业有限公司与苏州周原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其他合同纠纷”二审判决([2014]民二终字第111号)。
7.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刘来宝与阮荣林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终审判决([2014]苏商字第255号)。
8.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江苏华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扬州锻压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潘云虎等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再审案”做出的判决([2019]苏民再62号)。
9.《合同法》第52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10.这里所称的“无其他无效事由”可以理解为法定的强制性无效事由,即《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五种情形。
11.《公司法》第20条 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12.《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8条 合营企业获得的毛利润,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法规定缴纳合营企业所得税后,扣除合营企业章程规定的储备基金、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企业发展基金,净利润根据合营各方注册资本的比例进行分配。
13.国务院于1998年9月14日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外汇外债管理开展外汇外债检查的通知》(国发【1998】31号):“一些地方和单位未经批准擅自到境外发债和对外提供担保,或以保证外方固定回报等形式变相对外举债。”“严格规范吸收外资行为,坚决纠正和防止变相对外举债,包括违反风险共担原则保证外商投资企业外方固定回报的做法。吸收外商投资,要贯彻中外投资者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共负亏损的原则。”“今后,任何单位不得违反国家规定保证外方投资固定回报。”
2002年9月10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妥善处理现有保证外方投资固定回报项目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2】43号):“保证外方投资固定回报不符合中外投资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违反了中外合资、合作经营有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对于以合同外协议形式保证外方固定回报的,以及地方政府、地方财政部门、其他行政机关和单位为外方提供固定回报承诺或担保的,有关协议和担保文件应予撤销”(该《通知》已被《国务院关于宣布失效一批国务院文件的决定》〈国发【2015】68号〉宣布废止)。
14.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北京碧海舟腐蚀防护工业有限公司、邸建军、李依璇诉天津雷石信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做出的([2015]二中民(商)终字第12699号)判决。
15.最高人民法院就“强静延与曹务波等股权转让纠纷案”做出的(案号:[2016]最高法民再128号)判决。
16.最高人民法院“通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成都新方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58号再审)。
17.这里所称的“无其他无效事由”可以理解为法定的强制性无效事由,即《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五种情形;











